����| �}�H��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�pij
(�`�r) �W�s�ۦ��d��~�A��`ٱٱ�Ѥ@���C
�}�H�šA��W���ɡA�H�r��C���@�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F�A�J�y�f�뮷属�C�f�뮷属�H���A�p�J�~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H�B�j�����B�\�R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ﵥ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n�A�P�}�H�Ŧ��˱��B�P�m�B�P�ǩΦP�ת����Y�A�Ө��S�}�з����ᴿ���n�ʽæ��`���μs�F�٪����n¾�C�}�H�Ťj�i�H�q�L�L�̪����Y�A�Ѩ��@�x�b¾�A�M�ӥL却�ͩʫ�H�A�L�N�Ƴ~�A�@�ߥH�����B��z�m�����m�嬰¾�ӡA�s�L�s�ѡA�Ŵf�ǤH�A�q�ƱШ|�A���i�H���C
�L���֧@���Ӥ��֡A���]�L�N�s�Z�A�A�[�W�Զ��W���A���H���֡C�L��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��1989�~�ѥL���]�k�}�a��k�v���O��N�����X�̡B�㤧���G�̡��A�Ȧs�@�ʤT�Q�@��(�����|�w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��)�A�ѭ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ͦL��
�A�����ּܼ��O�ѲĤT�Q�T�ءC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ĥ|�Q�T���m�ҥӤE�벾���K���n�p��s�F���h���@�n�@�֤Ψ䧨�`「�ɪk��D衅�A�u�����Y」叙�z���v�Ƥ�
�A�i���ݥX���ӧO���֨ëD�}�H�ũҧ@�A�i��O�L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@�~�C(�d�ҥӬ�1884�~��1944�~�A�}�H�ťͩ�1879�~�A�p�G�O1884�~�A�}�H�Ť~�����A�p�G�O1944�~
�A�ĤG���@�ɤj���٥������C「�ɪk��D衅�A�u�����Y」
�A�P�v�ꤣ��)�q�T�H�O�}�H�ũҧ@���֤��A�i�H�ϬM�L�H�y�W�Q�A��`凛�M�A�R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ޡC
�q�ƴ���A�n���@�w����Ư��i�C�}�H�Ū����ˮ}�u�촿�Ш|�L:「�^�a�@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A�M�l�̥���Ū�ѡA�観�ަu�~�`�C」(���|�w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��)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p��:「�x�e�ئa�h�ئ�
�A�a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R�ѡC」�]���A�L���a�x���}�n���D�w�Ш|�M�RŪ�Ѫ��DzΡC�o�Ǯa��b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�h���ϬM�C
���D�n�{�Ѽ�
�����ͲP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_����n�w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A�B�ֵY�w�U���ѡC
�H�D
�Ѩӫa�í��n�{�A��ɹŦW���p�ӡC�U���O���s�@�ɡA�ʫ��v�@�p�ѫJ�C�x�Я���L��A�ߦa�w�Τ��ۨD�C�դU���a���h�f�A�X�O�ݦr�G�H�d�C
�o���֬O�Ҥl�۹D�A�@�إH���֦ʫ��A��s�ǰݡA�y�M�۱o���ߺA�A�D�M�ȤW�C
「�����ܤ۰��h��」�A「��g���ީ|�H��」�A「�̵M�a���@�ѥ͡A��D�P��@�ޯѡA」1938�~10��
�A��x�n�I�s�F�A�L�u�o���a携�a�@�p�����öQ�����y�A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a�����A�H�ЮѺ����@�a�ͬ��C
���n�{�ѼөM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A�L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C
��J�Ыn�{�Ѽ�
�p�_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A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k�j�C�ϻ�`�ʤT���ΡA�꽥���ѸU���ѡC�����J�лX�ʸf�A�I�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ǻD�s���h�J�g�A���Ұg���r�ݽѡC
�ܾԳӧQ��A�L�^��n�{�ѼӡA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ߪ��߮��A�L�g�D:
�A���Q�G��^�ٵn�n�{�ѼӥΪF�Y�D���P�h�ѫF��
�k�j¤�_���A��樣�n�{�C携���w�J�ǡA�u�S�����d�C�~�쩯���l�A���ͤ��ۨD�C���Q�Φܤ�A�M������S�C�~�P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դ�T�C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ɡA����ҧ�աC�ʫ��`����
�A�v���p�ѫJ�C�^���O����A��Ҥw�q�Y�C�_�ɩ��w�֡A�@���n�Q�B�C�T�_�����y�A�p��q����C
��F�C�Q���ʹª��ɭԡA�L�`���F�ۤv���@�͡A�P��ব�óo麽�h��
�A�ˤ��z
�o麽�h���y���m�A�L��o麽�h���y�A�q�ƱШ|�o麽�h�~�A���i�F�o麽�h�H���ӷP����h�w���A�Y�M�R���A�C���m�C�Q��z�h�n�C�ߨ⭺:「・・・・・・・・�n�Ӧ��f�e�}�X
�A���Dzר��ѾG�@�C���@�q�ߤ��O�x�A��P�f�fģ�ѥСC」
; 「・・・・・・・・�ѸS�Y�w�x�Q�U
�A�W������V�T�d�C�ʦ~���¦h�U���A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Ԯ��ӡC」���F�F���ߪ��߮��M�~�Ӻ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决�ߡC
�}�H�ŬO�ӦѾǨs�A������@�m�L�D�n�@�����A��
�A却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�e�U���y�N�A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Ӥ��]�A�Ҧp:
�����P�e�J�e�ӡA���ӽ֨÷P�o���C�]�t�ýl�T�ͬ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C�[�O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δ�况��n�ۨD�C���߿W������k�A�ӻy�f�H������C
�C�i �S叠�e��
�}�f�L�ݱ������A�Ȫe�M�L�~���A�C���p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A�}���p�m�@�`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źïd�W�E�A�ѥx��H���J�¡C�i���Z�a�߬����A�Ƨ@�۫����C
�M�Ӧb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��
�A�o���֥u���L�O�����峹�Ӥw�A�O�H�Y��٬O�L���ϬM�ܤ�Ԫ��ɴ��A�s�{�B ����_���e�᪺�֡C
1938�~10��12��A�饻�I���x�b�f�{�j���W�n���A���L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s�{�C�@�ɶ����n�b��A�s�{�@���̰ʡA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ۭ����D�k���A�l�өM���k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C17��Aĵ��^�R����a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s�{��i�V�áC�ʩm�ɯɦ��B²���装�A�ߦ�携���k���s�{�A�j�媫��B
�����B�Ϯѩe����ǡC�ĭx���{���U�A�����B
�q�O���w���Ӱk�C�U���o�|���m�H�D�n�C��
�A�N�O�O叙�s�{�N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O�Ƹ�:
�j���W�Y�b����A���D�H��J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ؤѹ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@�D�ū������ܡC�n����a�{����A�_�����_�w�L�n�C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A�@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p�{�C
�n���{�M��۶ʡA������Ӥ�X�^�C�צa�Ƚ����襫�A����H�֮��]�x�C�L�L��b�����b�A户���l³�Q�T�ǡC�ó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S�A�L�����h�_���ӡC
�x���U�ܨ����q�A�����~�D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Ԥ��M�s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n��槖�j��ˡC�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A�����Ϯѩe�D�ǡC�ڥ�E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A�´�^���f�M�ˡC
�F��v�ۨƥ_���A�\���j�줭�ϫ��C�g�D�u�g��J�g�A���N�ͧL���ڧL�C�d�t�ѥ͵S���V�A�ժ��Ҥh�w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A�G����|���n�C
1941�~12��8��A�ӥ��v�Ԫ��z�o�A�饻�I���x����A�}�H�ťظ@�ĤH���ɦ�A�˨���|��y���A�K���W�A�d�����W�A�L�g�U�F�D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n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y
�A�䤤�ĥ|�B
���B�C�T���A�g�ӻ����˪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
�̼��e�P�P�Ͼ~�A�M�C���~���סC�w�o�k�[�T��户�A����K������C
�饻�I���x�I�e�@�a�A����T���k�A强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w��
�A�Ѩ��~�L���n�C
���ְ��X�d���A�M�]���F�P�u�F�C�̮����`�`�P�q�A�����{�S����F�C
�饻�I���x�b����M�]�^��A�g�L���H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`�P�q
�A�_�h�D���T�r���C
��÷�ɨ����q���A�{�M���Y���e�I�C�H�y�����椣�o
�A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šC
��x�`�`�I����Y�A�e���Ϥ�R��H�h�A��H�X�����رa�}����
�A�_�h�|�Q�{���O�i��l�C
��x�e�⭻�䤧��A�}�H�Ŧb1942�~�@�צ^��s�{�A�ظ@�b��F�I�e�U���s�{�A�@����凉�}�ѡA�Z���_���A�X�\�H�b�Ⱦj綫�W�ä�A�P�䭥������ծI
�A����_�ʡA�H�ܤ��m�峹�]�u�n���@��Ϋ~�A����Y�a�A�L��o�ɪ��s�{��@�j�ӵ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I�h�a�g�U�F�m�H�D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y:
�V�x�L�~�j�����A�ثΤs���@�椤�C�ӻճs���h���a�A�_�j�ݥˤi�����C
�Ӫ�즤���^�A����ծI�B�B�D�C���쿳�d��ŭĽ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C
�e���Ƨ@�c�n�A�ȶQ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ť۵{�ѥ���A����Y�a�Ư��|�C
������訬���ȡA�E�ȹM�a�W�y���C���Ȳ��r�ܾ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P���N�C
���ɩ����῾���A���魫�[�ʷP�͡C���I�K�C�F���a�A��烟�s���M�a��C
�}�H�Ū��o�@���֡A�i�H�@���ٴ��a���ܤ�Ԫ��v�֨�Ū�A�ר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ɦ��a���H�ӻ��A�|�İ_�啕�ƪ��I�h�^�СC
�}�H�ŭȱo�H�̴L�q���a��A���ȶȦb����ѲW��
�A�@�ͭP�O���îѡB
�L�ѩM�ЮѡA�٦b��H�~������C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W�Q�A���i�H�q�F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|�A�S�O�O�ڵ��Q���A���@�L着�M�W���ͬ��A�]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ɴ��s�F�j�Ǫ��n¾�C�L�µ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j�Ǯɪ��ǥͪL��Ҳ��§�u(�L���ɥ��L�����s�F�ٱШ|�U���ݼs�F�j�Ǯժ�)�C�L���ְO��:
���ȸ߰ݬO�_���u�s�F�j��
�D�o����却�u�ѡA����﹪�d�^�{�C���Q�ǥۦw�^���A���V�H���@�j�ҡC
�L�b�m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۽ᨣ���n�g�D:
�e����S�@�~�A�����W�P���ؾE�C�m�c�@���ئA�q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|�s�C决���n���P���w�A����i��Y���P�C�զc�T�_�^���j�A�L���Ѩ��O�ʤѡC
�L�n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U�Ӫ����q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M�ۤv���M��
�A���@����H�\�G�����w�C
�[�@
�����ܤ۰��h�ݡA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ڤw��C�H�r�ӥx�{���n�A�ڶ����w�U�����C�ˮɦ��V�a�~��
�A�u�屩���q�R�w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Ѧۨ��A�ɯɸ��D�N�T�a�C
�}�H�ųo���m�[�@�n��
�A��L�����ߥ@�ɪ��յL��A�a�~�h���B
�u��w�R�O�@�^�ơA�i决���r���{���ӥx���A�h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l�A�Y�ϬO�u�q�ƱШ|�u�@�]�����C�墨�Ǹ������ᤧ�H��A���d�L�̬O���N�U�ӫa���A���L��决���|���n�U���C
�P�ˡA�L��咏���֡A�H����N
�A���F�F�L�M���a�ƪ��ʮ�:
「�����X�U��̱H�A�����g�o�J�C」�m���Ӭ��n;「���զ���[�ɼ�A�ұ�½�����]��C」�m�ȧ��n;「�l�`�D���å|�ɡA�s�ߪ������d�j�C」�m���ֳ��j�f��n�C
�}�H�Ū��֭��R�ݲM���A���֬y�Z�A�L�ת��g���j���ε��y�A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M�ӡC�L�����g��却���j��ˡA���ΧN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A�[�W���[羣��A�`�o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֤ߡA�j�`凛�M�����ڥ���A�P����ΦP�C�ҥH�H�̻{���L���m�n�{�u���n
���M�O「�l�Ƨ@�֤H」(�m�n�{�u��・���_�n
���|)��「�~��~�����ʯu」(�P�W)�A�֭����C�n�C���ڭӤH却�H���L�ϬM�ܤ�Ԫ����g���A�g�ӻa�D�d�n�A�P����s�P�@���աA�o���ӬO「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֮a���A��쿳�`�y�K�u�C」�}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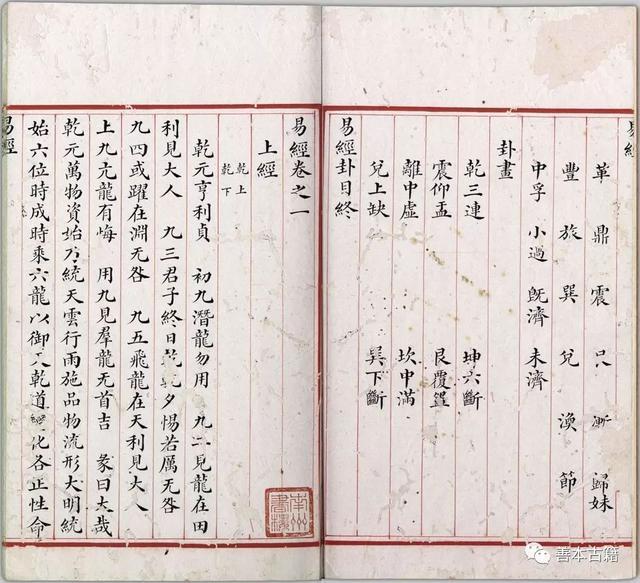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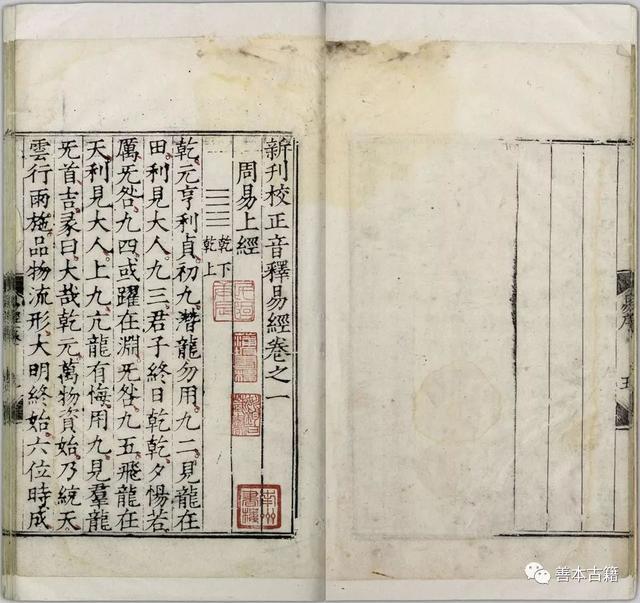
�}�H�ť��Ͷ�
|
��ƨӷ�: http://www.ifuun.com/a2018121717561331/
�s�{���p�_���O�ۦW�ӷ~�ϡA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A�C�H�p�V�C�p���樫�䶡���H�̴X�G�L�H���D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v��1928�~�A��L�H���D�o�̴����@�y�P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ɫئ�
���n�{�ѼӡC�n�{�Ѽ��îѳ̲��ɹF600�h�U���A�䤤�H�s�F���m�B�U�ٳq�ӳ̬����ơA�s�F�U���x���ä]�X�G���ơC���o�@�����H��1947�~�}�H�Ū��u�@�� �Ϯ������C
�n�{�Ѽӭ쬰�}�H�ũ~�ҫe�y�A�L�N���ج��G�h�p�ӡA�R�W�u�n�{�Ѽӡv�A�æ��D�֤��G�u�����ͲP�@蠧���A�_�s��n�w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A�B�ֵY�w�U���ѡC�v���~�O�}�H�ųu�@65�P�~�A�u�w���֡A�O�H���ѷP�n�U�ݡC
�@�ͱ��ЮѻP�îѤG��
�}�H�š]1879�X1947�^�W�Ю�A�r�H�šA�H�r��C�䯪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s�F�A�E�y�f��A�}�H�ťX�ͩ�s�F�^�w�A��E�~�s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p�_���^�C�}�a�@�N�ѭ��A��B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g�Ǥj�v�A�ڥS�}�Юִ��b�]���s�D�f�ɥ��s�F�٪��C�}�H��9������A�֦~�t�W�A���L�o�Ӧn�ǡA�C�C�`�]�W�Ǥ����C
�@
�}�H��1900�~�w�~��Ǯ���B��Y��١A1904�~�P�L��áB�J�~���B�j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H�B�v���p����´�s�Ӫ��A�C���ʸm�ϮѦ@�P��s�C�}�a�P�L�a�B���a���Y�K���A�L��ìO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Ӯ}�H�ū�Ӱ��F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j�j���P�C
�}�H�ŻP�s�Ӫ��P�����P�A�L��1904�~���u�쭻�s�����ǰ�ЮѡA�}�l�оǥͲP�A�ñq�����W�P�Ѭ���D���A�@�ͱ��ЮѻP�îѤG�ơC�~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ǰ�A�L�S�����Ш�f�����ǰ�B�s�����ǡB��s�����v�d�j�ǡB���n�j�ǡB�s�F�k��ǰ|�B���s�j�ǡB��Ԥj�ǡB�Щ��ǮաA�H�έ�����^�B���H���ǩM�D���Щ��Ǯյ�10�h���ǮաA�D����ǡB���v�B�j�y�ѥص��ҵ{�A����s�ۤF�m�����ǥv�n�B�m���N�����O�n�B�m����ѥؾǡn�B�m���ꪩ���ǡn�B�m��v�v�n�n�B�m�Ȭw�U��v�n�B�m�~�ѦD�k�ӡn�B�m�j�y��Ū�k�n�B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̡n�B�m����s�n�H�Ρm��ǻ����n���Q�h�رЧ��C
�}�H�Ū��ѲW�աB�v���Y�ԡB�ɤ߱оǡB������H�A�Ʊo�ǥ;����C�s�����Ǿǥ;x����A�̲ץѾǥͦ۾ܱЮv�~��_�W�ҡA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Ъ̶Ȯ}�H�Ť@�H�C�}�H�Ű���40�h�~�A������ѤU�A�s�{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n�j�ǤΤ��s�j�DZб��ΥɲM�B���s�Ϯ��]�]�����w�͵��A�����O�L���ǥ͡C
�����ͲP�@蠧��
�}�H�Ŧ~���a�h�A�ʤ��_���|�Ҹե�Ū�ѡm�Q�T�g�����n�M�m��v�qų�n�A�L��Ӧ]�Ƿ~�u���A�峹�뵴������Ǫ��A�n��~�E�����ʦ��G�ѡC�o�K�O�L�îѤ��l�A�]�o���}���A�ϥL�ƥ[�÷R���ä��ѡC���ЦU�a�ǰ��A�L���`���Y���A�n��O���ʱo���֩t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A�f����B�F�ѮѼӵ����X���îѤ]�h����ұo�C
1928�~�A�s�{�p�_�}�v�����A�}�H�űN�~�ҫe�y��ج��G�h�ӥH�îѡA�١u�n�{�Ѽӡv�C�Ӥ����e���y�A�U���G�h�A�~���K�]�A�ӤU�����U�A���k����ô��q�ϮѡA�ӤW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A���k�G�ǧ��üs�F���m�C�L�����D�m�n�{�Ѽӡn�֤��G�u�����ͲP�@蠧���A�_�s��n�w�~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
�A�B�ֵY�w�U���ѡC�v
�n�{�Ѽ��îѬ��סA�̲��ɹF600�h�U���A�䤤�H�s�F���m�B�U�ٳq�ӳ̬����ơA���ٿ��x�ΦU�a�X�����Z�]���ơC�ΥɲM�б´��b�n�{�Ѽөܾ\�Ƥ�A�����m�n�{�Ѽө��üs�F�ѥءn�A���s�{�j�ǡm�Ϯ��]�u�Z�n1935�~�ĤG���Ĥ@���A�@�C�X�ѥ�480�h�ءA�䤤�\�h���M�s�F�W�a�@�~�C1940�~�A�����|��s�F�媫�i���|�A�n�{�ѼӰe�i�����`�סm�s�F�q�ӡn�A�Q���{���t���C���~�|���U�جöQ�����m�M���ƺءA�θ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Τj�q�����襻�C
�}�H�ŶݮѬG��
�}�H�ŶݮѦp�R�A�ʱ��ǻ��C�L���n�{�ѼӡA�@��H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A�ӷQ�Ѿ\�䵽���μs�F���m�N�����C�}�H�Ź�Ѽө��è��y�����ܤH�A�u�����~�P��p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n�j�DZб��ΥɲM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ѼӾ\���s�Ѥ@�Ӧh��A�ñN�ӮѼөҦ��üs�F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m�n�{�Ѽө��üs�F�ѥءn�C
�}�H�ų��w�N�@���j�y���e�@�B�G�U���O�B�A��ت��O�ϤH����o���ѮɡA�H���ݯʤ����A�K���A�V�L�ɾ\�C�L�o�˩�Ѥ��ê��ǻ��A�P�Ϩ�a�H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ä��ҡC�}�H�ŨC�Ѧ^�a�A���w�˨��îѫǾ�z�j�y�A�ι�j�Ѷi���I�աC�J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L���D���A��²�N��A�Χۿ���`�]�A�ӹJ���t���A�L�h�n�ۤv�A�g�Ƴ��C
�}�H���îѻ������֥X��A�Y�ϬO�̦n���B�͡A�]�n�Ѽ��æ��ƥ��~�֬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o�L�}�H�Ŭ����ϮѪ��ѪB�ͤ��@�A�}�H�Ŧ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s�F���m�ѥ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g�n���Ǥ�g�D�G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P�E�P�����s�j�DZб¡A�@�Ʀ��~�K�K�Eų��j�X���ۡA�O�s�����A�G�n�{�Ѽӭe�æ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|�H�����A�p�}�Τs�����~�A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ջﶰ�A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t���]�C�E�]���ƥ��A�G�����N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C�Ӷ������b�ӮѤ����G�u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A���Ǥ�ҭz�̥~�A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���A��r���A���W�ۦ����s�п�Z�Z���A�ԫʬ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C�v
�n�{�ѼӪ��̹B
�@
�u�n�{�Ѽӡv����D�T�B�C1932�~�A�s�{�]�B���a�A�}�a���v�Z�y�ɶ�A�Ǥ��îѤ���ήɷh���A�H�P�h�c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ȼߡA�}�H�Ŧ]��卧�f�֤�A�ߵh�U���C1938�~10��A�s�{����x�I���A���s�j�ǩ^�R�h�E�A�}�H�Ŧ۷P�~�ѡA���ղv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îѤ��_�J�Ĥ�A�L�N�����Ѥ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A�H�s��j�Ƕ����s�Ϯ��]�έ���J�ҡC1942�~�A����_���A�}�H�ŤS�_�N���y����B���D���J�ҡA�ڻ��A���ɥξ��|��B���D���̳Q�g��ҧT�A�ѽ���B���D���̤S�D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A�i�l���G���C
�}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A�ͬ��a�x�A�Ʀ��Q���X����y���͡A�o�_�M�ڵ��F�L��æb�J�ҿ�s�F�j�Ǫ��u�СA�ټg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u��L���F�v�̡A���{�F��W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C
�ܾԳӧQ��A�}�H�Ŧ^��s�{�A���N�T��s�Ѿ�z�s�ءA�E�]�k�N�s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y�B�^�C1947�~�A�}�H�Ŧ]��Ŧ�f��o�u�@��s�{�A�צ~69���C�n�{�ѼӪ��îѦb�}�H�ťh�@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j�ǡ]��֤J���s�j�ǡ^�Ϯ��]�B�s�F�٤��s�Ϯ��]���ʥ~�A��l�����p�ɡC
|
|
 ���۬u�g�H�ť���
���۬u�g�H�ť���
�}�H�ŵۦ� �s�F�îѬ��Ƹ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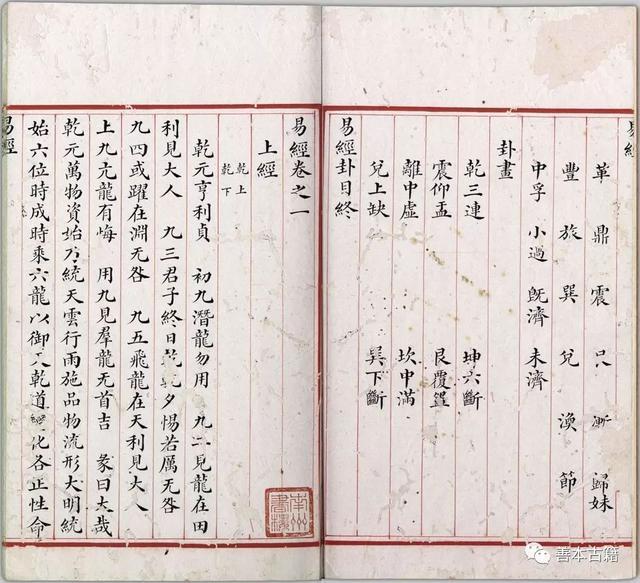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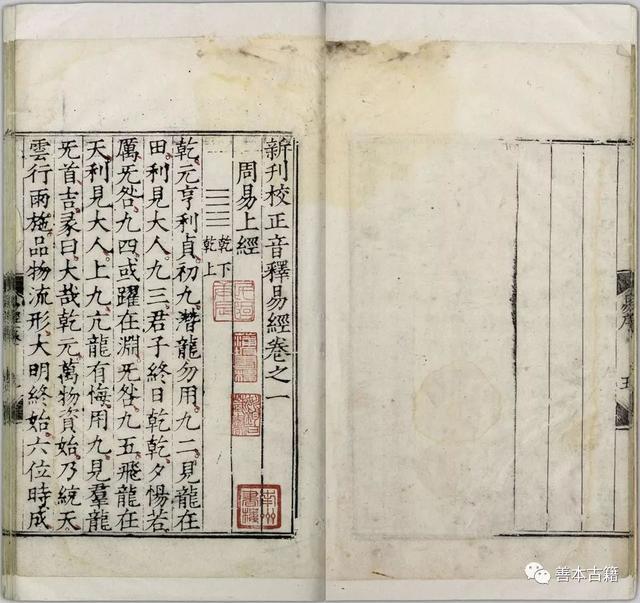
 ���۬u�g�H�ť���
���۬u�g�H�ť���